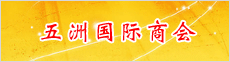青藏公路边可见现代垃圾

几乎化完的雀儿山之雪

姜古迪如
原标题:长江可能越来越短 经济活动怎样改变了生态?
姜古迪如冰川位于各拉丹冬峰西南部,意为“狼群出没的冰川地带”,由南北两大冰川构成,冰舌海拔5400米。数百年以前,南北两条冰川的末端曾连在一起,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两条冰川逐渐分离。
我国曾在1976年、1978年两次派出江源考察队至长江源头考察。根据水文地理等资料,1979年正式确认沱沱河上游的姜古迪如冰川为长江正源。
唐古拉山镇
唐古拉山镇地处青藏高原腹地,位于青海省西南端的长江源地区,号称万里长江第一镇。长江正源沱沱河位于境内,全镇平均海拔在4700米以上,是青藏公路上的重要驿站,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全镇辖区面积达4.9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乡级行政区之一,接近半个浙江省的大小。
玉珠峰
玉珠峰又称可可赛极门峰,海拔6178米,位于青海格尔木南160公里的昆仑山口以东10公里,是昆仑山东段最高峰。南缓北陡,南坡冰川末端海拔约5100米;北坡冰川延伸至4400米。
□晚报记者 劳佳迪 青海摄影报道 制图 邬思蓓
入睡前,寒梅惯性凝视恰好投入窗口的北斗七星。冬夜清澈,斗柄指北的七颗星一览无遗。最黯淡的天权星也将光点投射在白壁上,影绰之状竟比暗黑夜空中的真迹更显明亮。
星夜与一年前的别无二致。那时她站在长江正源姜古迪如冰川的冰洞中,也曾透过“天窗”寻找北斗星。但前不久故地重游时发现,当时足可容纳400人站立的冰洞已消融得了无踪迹。
位于长江上游的这些固体水库,正在以加速度人间蒸发。这让多次作为随队医生溯游而上的寒梅充满忧虑:若长江变短了,沿江经济带该怎么办?
探险队员怎么说?
雪山脚下迷宫般的冰塔林不见了
根据水文地理等资料,1979年沱沱河上游的姜古迪如被确认为长江正源。此后的三十多年间,知名高山病医生寒梅多次亲身探访这位“母亲河的母亲”。
当记者找到寒梅时,她刚从姜古迪如发源地各拉丹东雪山回到唐古拉山镇。说明来意后,寒梅拿出今年10月25日最新拍摄的格拉丹东图片,用手指画着圈,从图上看,她画圈的位置是一片深褐色的沙砾。
“原先这里不是这样的,山脚下是成百上千个形态各异的冰塔林,现在都融化成了沙梁,10月底我们的队伍走了一个小时的路,只找到两个冰塔,延伸到很远的冰舌变短了,都露出黑石头。 ”
寒梅告诉记者,因为近几年冰塔的急剧减少,她还曾闹过笑话。“2002年我走冰塔林时觉得非常容易迷路,所以2005年《再说长江源》剧组进去时,我特别关照要3、5个人结伴走,结果剧组出来都感觉我在小题大做,短短3、4年,以前有2层楼那么高的冰塔要么化了,要么缩成了一层楼。 ”
据她回忆,2001年7月第一次进入各拉丹东,冰塔林距离大本营特别近,走路半小时就能触摸到冰川,“2002年进去,也是7月份,嘎曲河还是从冰面上直接开车过去,后来几次是5月份进去,冰却基本化完了,泥潭里还陷了车。 ”
印象最深的还是2011年10月进入时,寒梅发现姜古迪如北冰川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冰洞,是一年前未曾得见的。 “这冰洞也是融化过程中出现的,足能容纳3-400个人站立,三个老乡向导进入了,我在洞口喊,他们居然听不见声音,可见一年中掏空了多少冰。 ”
寒梅与另三人结伴进入后,发现洞穴中间竟还开了一扇 “天窗”。10月雪水依旧在滴答,顺着河床流淌而下。当晚,她扎营于此,却未想只有一面之缘。今年10月底再访姜古迪如时,冰洞已融化得不留痕迹。
“通过1969年和2010年卫星图片对比,姜古迪如北支冰川退缩700米,南支冰川退缩了1200米。 ”去过各拉丹东山头另一端的杨欣还告诉记者,作为长江南源当曲的大支流,长江源最大冰川岗加曲巴退缩速度更为惊人。
杨欣是绿色江河环保促进会会长,也是中国民间环保界的灵魂人物。 “2005年到2010年我们进行了连续的实地监测,2010年的结果与1969年的图片对比,岗加曲巴冰川最大退缩距离达到了4公里。 ”
记者看到了什么?
著名的“雪馒头”变成了“冰帽子”
长江正源的两大冰川退化如斯,而这只是孕育了亚洲7条最重要河流的青藏高原上寻常的一幕。玉珠峰,昆仑山东段最高峰,其南北两坡的冰川被寒梅和杨欣称为 “融化得不算太严重”的样本。
但记者还未抵达玉珠峰,一路便已故事不断。不少常年跑青藏线的运输司机提醒,经过可以观览北坡全景的西大滩时,应该留心下冬季原本白茫一片的山头。可可西里管理局副局长肖鹏虎也打预防针:“11月刚下过两场大雪,但西大滩还是有大片灰褐色岩石盖不住。 ”
果不其然。记者在西大滩看到玉珠峰山坳中留下了许多纤细的流雪痕迹,可以想见曾经的银装素裹。而当靠近末端海拔5100米的南坡冰川,曾多次登顶玉珠峰的索南达杰保护站站长文嘎止不住感慨 “退得太多了”。
记者看到,冰舌一段夹杂了很多逐渐被冰层剥离的石块和灰尘,冰柱下更是堆积着冰川消融后残余的沙丘。而在距离玉珠峰冰川主体几百米处,还堆放着大量土石废墟。文嘎告诉记者,这是冰川融化很直观的标记物,可以窥知冰川曾经延伸到的地方。
走近冰川,记者发现触手可及的表面不仅被融水划出几道几人高的融水槽,冰川下方的土石层周围也漏出巨大缝隙。据文嘎介绍,直接暴露在阳光下的瓦砾显然更容易吸收热量而带动冰层融化。
尽管时值隆冬,行走在冰川上,依然可清晰听到冰柱爆裂的声音间或出现。文嘎指给记者看记忆中冰川过去曾经延伸到的地方,视觉上感觉至少消退了1/3。
对于玉珠峰冰川的体量,杨欣则笑言“小儿科”。据他通过地理遥感信息、卫星图片与实地监测的对比,近30年长江流域冰川退缩整体呈现加速度,令“雪馒头”纷纷变成“冰帽子”。
其中,贡嘎山的海螺沟冰川退缩约1000米,雀儿山冰川末端在垂直高差上退缩了大约200米;雪宝顶冰川的末端在垂直高差上退缩了大约300米;玉龙雪山最大的白水1号冰川冰舌大约后退了250米以上。
记者2009年搭乘班车时也曾穿越号称川藏北线第一险的雀儿山主脉。当时司机曾坦言,过去行至雀儿山总是提心吊胆,因为道路上积雪满坡,极易滑坠。而记者看到的情况却是,即使是向阳面,山顶上依旧稀疏盖着薄雪,遍布流雪痕迹。
当地人生活受何影响?
房门被沙堵 单位面积产草量少了50%
记者来到万里长江第一镇唐古拉山镇,注意到长江上游住民的生活细节已最先感受到冰川退缩。牧民龙珠告诉记者,每年到了相近时节,便要将家中驯养的羊群赶到湖心岛上啃草,这两年却发现冰面越来越不结实,羊群不敢踏冰过河。 “就这两年比,去年10月冰面结冰已经很厚了,今年10月却还在打雷。 ”
在龙珠的记忆里,“冬打雷”现象在气候干燥、冬天漫长的唐古拉山镇几乎没出现过。而科学分析,冬季打雷正是说明空气湿度大,近地面层的暖湿气流较强,与地面上空的冷空气交汇后产生强烈的对流,便形成冬雷。
建在沱沱河大桥一岸的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管理员吐旦旦巴则告诉记者,虽然年年冬日皆多大风天气,但今年却在保护站背后形成了大型沙堆,是去年建站时未发现的新现象。作为该保护站的创立者,杨欣对记者分析,这也是上游冰川消退后沙化加剧的表征,由于周围无阻挡物,沙砾便随西风、北风长驱直入。
杨欣表示,整个全球气候变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冰川变化。 “因为海水和气候的变化没有专业仪器是测不出来的,冰川则是生物多样性的最顶端,其退化存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据悉,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三江源地区。
在公路边开了一家藏式茶馆供过路车歇脚的扎西也告诉记者,过去10月份就开始储存过冬的风干肉,“每年年底当气温在零度以下时,我们将牛羊肉割成小条挂在阴凉处自然风干,到来年2、3月食用,现在不得不推迟一个月。 ”
记者从沱沱河水文站的一份针对1960年到2009年每10年温度变化示意图看到,1960年到1969年平均温度不到零下4度,2000年到2009年平均温度上升到零下3度,直接上升了1度。
而在同样沙化严重的黄河源区,曲麻莱县麻多乡郭洋村书记索南仁青还清楚地记得,十几年前黄河源头附近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景象,“原先冬天冷得羊会留鼻血,现在却越来越暖。 ”
一直生活在黄河源头附近的色洛家5年前有300多只羊、70多头牛,而随着沼泽沙化,如今只有30多头牛,一只羊都没剩下。据统计,在三江源有90%左右的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和50年前相比,单位面积产草量下降了30%-50%。而从三江源生态保护区搬离草场的牧民已经超过3万人。
冰川消融有何经济危害?
沿江经济带将面临“缺水”的隐忧
就在草场沙化加剧的同时,江河的径流量却出现了“回光返照”。记者驱车到位于索南达杰保护站与五道梁之间路段的长江北源楚玛尔河查看,虽湖面上盖着看似厚实的冰块,却能在多处找到破冰而出、潺潺流动的活水。据肖鹏虎介绍,过去每年冬天楚玛尔河都会断流。
记者从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了解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雅鲁藏布江干流四站中地下水和融水补给总量达到了径流补给量的50%之多,而布曲流域受冰川退缩影响,增加水量940万立方米,长江出源径流的总体影响估计达到了0.19亿立方米。
沱沱河水文站为记者提供的数据也显示,2005年沱沱河径流量为15亿立方米,2010年冲高到20亿立方米,为史上最高,与1960年相比激增167%,降雨量亦从1985年的冰点150毫米剧增到2010年的500毫米。
但遗憾的是,江水增多却难以为继。青海省三江办副主任李晓南就对冰川持续融化带来的经济 “负能量”倍感焦虑:“长远看,全部冰川、雪线都没了,必会导致源区水源枯竭,中下游就会枯水、断流。 ”
中国科学院一份研究咨询报告中也写道:“从长期看,随着冰川的持续退缩,冰川融水将锐减,以冰川融水补给为主的河流将有可能面临逐渐干涸的危险,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及生态与环境将产生严重影响。 ”
以黄河源区耶合隆冰川为例,其在1966—2000年期间退缩了 1950米,2000年的长度只有 1966年的23.2%。该地区在2000年以前的34年里,它的年冰川长度退缩速率是小冰期至1966年间相应退缩速率的9倍之多。
而黄河断流已时有发生。 2003年年底,黄河源头鄂陵湖近30多米宽的黄河河道裸露在外。 2005年3月河南郑州亦出现黄河干枯。最严重的黄河断流则发生在1997年,一年断流多达226天,仅给山东一省造成的损失就达135亿元。
记者当地考察还发现,冻土退化已影响到青藏高原上道路的效能。在纳赤台至不冻泉路段,记者多次看到路面开裂。据专业人士介绍,这是因为沥青混凝土路面下多年冻土上限都在下降,特别是高温下高含冰量路段的下降幅度达到了4米左右,致使路基下沉变形,随年平均地温升高而剧烈变化。
另一个潜在危机是:由于湖泊水位随冰川融水急剧上升,近湖公路基础设施、输油管道等暴露于随时被淹的风险之中。
经济活动怎样改变了生态?
剖开死牛肚子发现塞满现代垃圾
而对于长江上游的冰川退化,杨欣、寒梅、肖鹏虎等人都对记者分析,最主要就是因为气候急剧变暖的大环境,但也不能否认人类现代经济活动对这一负面进程的加剧作用。
近两年唐古拉山镇已逐渐重视垃圾治理,但考察现状,要彻底解决垃圾危机却显得殊为不易。记者在唐古拉山镇上看到,虽然刚被清走一批垃圾,镇上的公用垃圾桶内仍是满满当当,不少生活垃圾更是随意散落在周围。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垃圾桶均有焚烧过的迹象,塑料容器的表面皆被熏黑。记者从熟悉镇上情况的一位人士处获悉,唐古拉山镇有一辆垃圾车,是由格尔木市环保局直接代管,但负责倾倒垃圾的环卫工人隶属镇政府,却常年经费紧张。
由于连油钱都无力支付,环卫工人处理垃圾的方式往往是粗暴地付之一炬,并且没有固定时间规律。至于焚烧垃圾产生的危害物质二英,虽然官方和民间机构都曾重点宣讲,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难跨资金阻碍。
在唐古拉山镇以东通天河沿岸,记者也看到纸箱和封装带随风飞舞。记者离开唐古拉山镇后,抵达进入西藏后的第一个县城——安多。当地一位牧民甚至告诉记者,前几天家中死了7头牛,剖开肚子竟发现都是黄色的垃圾袋,“东面的草场本来很肥美,现在都是白色垃圾,到了夏天苍蝇多,气味重,遍布整条山沟。 ”
记者2010年走川藏北线,途径由昌都通过那曲的黑昌公路时,也曾被满坡垃圾震惊。尤其是索县、巴青、丁青路段,由于风向缘故,各种塑料瓶被大风吹至山沟中积聚。回家整理照片时,记者甚至发现有数张取景优美的照片放大后查看细节,都出现了饮料瓶的踪迹。
对于垃圾来源,以唐古拉山镇和安多县为例,大多来自过路车。多位志愿者也都对记者坦言,针对本地人和暂住者的宣讲比较容易,但对过路人几乎很难展开环保灌输工作。
以玉珠峰为代表的景区,垃圾问题则更多来自游客。记者在通往玉珠峰的土路上看到,虽是冬天,鲜有游客,但进入保护区后,草地上仍残留着一些难以降解的现代垃圾。 “有些车辆车窗一摇就有大包垃圾扔出来。 ”索站站长文嘎告诉记者,每当夏季游客来访升温时,保护站每个月都要处理大量垃圾,20平方米的垃圾坑轻易就能填满。
为了改变现状,绿色江河长江源水生态保护站启动了 “垃圾换食品”活动。 “我们将产生的垃圾全部统一用编织袋装好,集中带到保护站,站里有一个垃圾打包机,先将垃圾通过臭氧杀菌,再分类打包,明年希望推动一个项目,由过路车辆将垃圾带到大城市的固定处理点。 ”但管理员吐旦旦巴也坦言,与过路车的合作还存在许多现实障碍。
◎记者手记
在长江源的一所民间保护站内,每一个到访的志愿者都要先看两部电影。第一部是彭辉导演的纪录片《平衡》,另一部来头更大,是当年和小布什争天下的戈尔自编自演之作 《难以忽视的真相》。
记者也在一个午后完成了这场仪式感十足的精神观礼,外面则是应景的沙尘暴。 《平衡》讲述的是在十多年前,那时可可西里还是一片环保事业的无主之地,一群人如何艰难地播种信念的种子,直至失去生命。
它像是一部荡气回肠的心灵史诗,尽管在最后将格外沉重的体制困境残忍剖开,令人最震撼的仍是正义之士与疯狂猎杀间的殊死搏斗,因这萤火之光最终挽救了即将灭亡的藏羚羊。
而如果看了《难以忽视的真相》,我们就会明白人类无论作何努力,都只是一场注定遗憾的悲歌。人类不过是在通向自身灭亡的道路上,圆一圆救世主的梦想。
片中随幻灯片不断揭露的灰暗现状,带给观影人的只有庞大绝望——毫无疑问,人类依存的地球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终点,而在这道自然命定的残酷法则面前,不断演绎产业革命、推动现代化的人类本身又是送葬人。
从这个角度看,现在讨论如何挽救地球为时已晚。凭借一己之力,我们无法再造原野和冰川。所有带有经济标记的人类活动都将是不可持续的,人类的宿命并不由人类书写。
不过,此时再回头重温 《平衡》,天空仍可以是明亮的。正如人生而会死,在这个注定的恒久的悲剧中,我们不都在向死而生吗?所以,就多一些电影中的悲歌吧,那是人类灭亡前曾经生存的善良记忆。